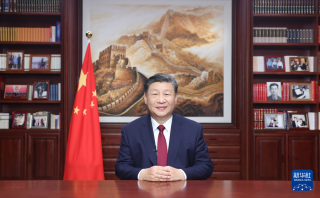秋瑾留学日本史实重要补正
辛亥革命网 2018-09-17 09:25 来源:《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 作者:章念驰 查看:
秋瑾两次赴日留学,在她光辉的一生中是极重要的一页。这段史实,过去因受到资料限制,记述简略,说法不一。今春,日本岗山大学教授石田米子先生寄赠我许多秋瑾留学日本时的原始资料,其中不少是秋瑾在日本就读的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资料,这部分资料由该校山口典子先生整理和收藏;还有当年带领秋瑾前往日本的服部繁子先生最新公布的回忆录,以及服部繁子的女儿贺来顺子先生收藏的两幅由她母亲绘制的秋瑾像。另外,日本中国研究会理事——久保田博子先生将她撰写有关秋瑾留学日本的大作寄赠了我。这些资料有的在日本已公开发表,有的尚未发表,而在我国则均未翻译发表。我院何凤园同志花了许多时间翻译了这些资料,使我得以窥见秋瑾留学日本前后的种种史实,这些史实显然与我们国内过去的各种记载有很大出入。今秋,我参加光复会学术讨论会时谈及此事,许多同行热切希望我撰文补正这段重要的史实,因而草就此文,以冀史家再进一步加以研究为幸。
一、秋瑾留学前的状况
以往各种史书所记载的秋瑾留学前的状况是:庚子之役之后,秋瑾耳闻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暴行,使她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凶残面目和满清政府卖国嘴脸。次年,《辛丑条约》签订,豆剖瓜分,国将不国,增加了她对祖国前途的忧忿。她从吴芝瑛(吴汝纶侄女,廉泉的夫人)那里读到了当时一些新书新报,视野不断扩大,思想境界不断提高。那时她与丈夫关系日益恶化,使她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之叹,曾一度离家出走,穿男装,放天足,上戏院,取号“竞雄”,欲与男子竞赛争雄。就在这时候,她与服部繁子相识了。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录中也有如此记载,但是比我们以往记载翔实得多。服部繁子(1872—1952,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博士是东京帝大教授,因受清政府邀请,至京师大学堂任教,其妻随至北京)的回忆录原名为:《回忆妇女革命家秋瑾女士》,原稿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发表在1951年日本《中国语杂志》六卷一至三期合刊上,这已被介绍到我国。回忆录的中下篇原稿过去保存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会,直到近年被该研究会仓石武四郎发现,才于1982年9月在《东西交涉》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服部繁子在她回忆录后半部分以较多笔墨回忆了她与秋瑾认识经过,彼此的交谈,互相的访问,很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秋瑾当时的思想面貌。
服部繁子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明治三十五年(按:1902年)8月,清政府请我国政府派人帮助在京师大学堂施行新教育。政府决定派我的丈夫去。……我也偕丈夫同往。……九月初到北京。……不久,吴芝瑛夫人来访问我,……此后我常去她家。
到了明治三十七年,正月里有一天,欧阳夫人来了,说:“……想建立一个妇女谈话会,常常聚在一起,相互研究,交换知识,所以,请您多加指教。”我听了很高兴,非常赞成,并商定了建会的日期。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个会馆里举行了妇女谈话会的建会式。……二月的一天,谈话会在欧阳夫人的家中举行。……有欧阳夫人、吴芝瑛夫人、陶大钧夫人 (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时一样,先读中国的书,然后读高等女子学校一年级程度的书,围遶这些提问题,随便交谈。在随便交谈的时候,一个女佣进来了,在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欧阳)夫人想了一会儿,便与我打了一个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有点为难似地说:“我的一个亲友现在来了,说是想入会,允许吗?”我说:“很高兴见她。”夫人就把那个亲友带了进来。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亲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长的身材,稍朝前弯曲,浓密的黑发披着,穿着男装,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蓝色的西装,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较长,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手杖,肥大的裤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着緑色的领带。脸色青白,大眼,细鼻,薄嘴唇,一个挺潇洒的青年人。欧阳夫人说:“师母,这就是我的朋友。”一语未完,那个青年便大声说:“王秋瑾!”我伸出手与她握了一下。吴夫人对我说:“师母,您不要见怪,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来这是一个穿男装的女子。吴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说:“给师母行礼!”那个妇女笑了笑,丢开手杖,给我行了个半跪礼。我用两手扶起她,让她坐在旁边的位子上。她讲浙江口音的话,讲话讲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欧阳夫人做翻译。我首先按照中国的习惯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住在前门外。欧阳夫人说:“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门外的一个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钧,花钱捐得一个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户部主事的官。),这位太太很喜欢读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男装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说话,一个劲地与二位夫人说话,三人都说南方话,不好懂。谈话似乎很激进,吴夫人脸露难色,欧阳夫人看看我的脸色,后向王夫人(秋瑾)使了个眼神。陶夫人和女儿先告辞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诗。
吴夫人对王夫人说:“妹妹,今天是谈话会,既然加入了谈话会,就要向师母请教”。王夫人点点头,看着我,问:“请问夫人,您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说:“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来:“孔子的信徒!那么,就是‘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原话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的信徒了?”欧阳夫人和吴夫人担心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来,说:“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说的‘女子和小人难养’中的那个女子,据说有另外一种意思,这句话,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说是一种格言。现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说女子有学问害多益少,这可以说是对妇女的侮辱,为什么要让别人这么说?我们就必须有修养。我一向佩服中国妇女的勇气和好学,我们都是妇女,要超越国境,相怜相爱……。”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语,欧阳和吴两夫人向我频频点头。
二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对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炉前,上次约好的,今天秋瑾来访问我。和上次不一样,这次她显得较沉着。还是穿着蓝色的肥大西装。我让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欢她,她是一个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长着象林黛玉一样的修长身材,加上她走路时的风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说:“秋瑾,听到你的名字,让我想起白乐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诗原文为:“风露飒已冷,天色亦黄昏。中庭有槿花,荣落同一晨。秋开已寂寞,夕殒何纷纷!正怜少顔色,后叹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怀哉聊一陈。男儿老富贵,女子晚婚姻,头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后时不获已,安得如青春?”)诗,那首诗让人感到妇女的悲哀,而你却不同,很幸福。”秋瑾说:“我的名字似乎是从那首诗取的,后来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穿男式西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看看我原来的猜想对不对。”秋瑾说:“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国,男子是强者,女子作为弱者永远受压迫。我想有一颗男子一样的强者的心,这样,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会是男子的心。发辫是夷族风俗,不是中国人必须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装。夫人,是不是这样?”
我轻轻点点头说:“这样你就如愿地成了强上加强的人啦!”秋瑾有点难为情,说:“是的。”
我怀着可怜的心情望着她说:“我的意见和你有点不同,女子决不天生劣于男子,作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论孝道的时候,没有光说孝父,而说孝父母,也就是说在家庭里,男女是同权的。你的穿男装的想法充满幼稚。羡慕男子而形态上模仿男子,不如说这是一种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装,但不能改变身体的组织。女子永远是女子,并不可耻,要堂堂正正地让男子敬慕。”秋瑾睁大着眼看着我,说:“夫人说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点点头,说:“可以,随你的意。另外,我想问问你的家庭。”
听她说,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个财産家(王廷钧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两岁,二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比她年小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握着秋瑾的手笑了,说;“那么,在你的家庭里,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个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国有句旧话,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这种模范,你丈夫是这个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说:“夫人,我的家庭是过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强暴一些,强暴而压迫我,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以更加坚强的决心对抗男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为了所有妇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干男子也不能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