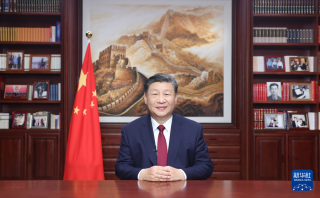辛亥武昌起义前后我的见闻及经历
辛亥革命网 2018-03-27 09:25 来源:宜昌政协 作者:沈刚伯 查看:
报秋之叶
辛亥(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也是亚洲历史上开新运的一年。因为那年秋季,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推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政体,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使一向听人宰割的东亚以此大梦顿醒,竟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地走上了独立自主之途。我那时正当志学之年,恰巧在武昌读书,很幸运地亲耳听到第一枪的响声,亲眼看到旧政权的崩溃。在革命前后短短两年内所见所闻的一些小事,虽然值不得历史家一记,但是在我看起来,却都像报秋之叶,很可因小以喻大。至于那次事变对我个人的影响,则尤为重要。因为革命后,国事未定,学校停课,我遂有两年多未能受到正规 教育;而且恰于此时离开家庭,投入社会,在那空前动荡、急剧转变的环境之中,逐渐体验到人事的复杂和世路的险恶,深觉现实的世界与书本上讲的许多道理及平时听到的一些学说多不相合。因此不由自主地常把实际的生活拿来和以前所受的教育互相印证,加以损益,而慢慢形成我个人的人生观以及一切立身处世的态度。那自未必就对,不过既已形成,便很难再改;我自信当年若是处在另一环境之内,则我个性的发展大半是不同于今日的。数十年来,我每忆当日的经过,辄自觉像一不识不知的村童突遇到“怀山襄陵”的洪水,眼睁睁地看着它始而浸润渗漉,继而汪洋泛滥,终乃把好些脊土灌成活壤,也把若干城市沦为泽国,把多年污秽洗涤净尽,也把新积的渣滓沉积下来;更看到它救活了一些辙鲋困龙,也放纵了许多毒蛇恶蛟,暴露出种种浑水摸鱼的狡诈暴行,也吞噬了好些负薪“搴茭”的仁人志士。目睹龟玉之毁,心惊虫沙之制,叹衔名之徒劳,怀归壑之无日;此身虽幸而尚未被浊浪卷去,也总免不了要痛定思痛,慨乎其言!我现在正是本着这样的情怀,来写一点五十年前的见闻经历。
山雨欲来
在保皇堂成立不久以后,当慈禧母子仓皇西奔之时,唐常才等谋以自立军起义于湖北,未成而被杀。革命运动之与武汉发生关系实自此始,可是他们当时在长江上所吹起的一点儿微波瞬即消失,并未能引起一般老百姓的注意。又平平淡淡地过了六年,而有徐锡麟起义安庆之举。安庆密迩湖北,那样传奇式的事变自然很令武汉人心震惊,但还没有能使群情愤怒。哪知此时偏有些不晓事的官吏妄想借徐案以兴大狱而邀功,竟株连到秋瑾女士,置之于死;这一下却把武汉三镇的老少妇孺都激动了。因为她是一个办教育的弱女子,未食清禄,未犯国法,徒因有人挟嫌诬告,既无证据,又缺口供,便被那个做知府的旗人处以极刑,那实在是任何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冤狱!当时全国刊物上登载的抗议和哀挽文字,若是汇编起来,怕不在百万字上下。尤其是几种薄本的秋瑾女侠小传竟风行一时,几乎人手一编,成为彼时见面时的谈资。那般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们此时大半都是十八九岁,血气方刚,见义勇为的青年,读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句子,还能不悲愤填膺吗?东路高等小学堂的学生胡养上书张香寿,请其独立,便在此时,可是革命的种子已经这样播种下来,开花结果,只待时日了。这种情形,当时在湖北的一些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张香涛本人便是那中间的一个。他那年秋天,离鄂入京,去做军机大臣,在火车上,对那些送他到信阳洲的门生故吏们做了好些诗,其中有一绝句,是“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泮桥儆杜鹃。可惜李、虞、文、谢辈,空随落日坠虞渊!”他借用北宋轻视南方人的故事来讽刺满清之薄待汉人,更以那几位籍隶南方的李虞诸贤自比,以明他虽有安邦之心,而不遇可为之时,纵令以身相殉,亦终无补于亡。这种说法该是何等的明白显露!果然,他死后两年,即发生保路的风潮。川粤汉铁路国有之,在理论上讲,原是无可訾议之策;但就事实而论,却与当时川、鄂、湘、粤四省商民及知识分子的即得权利发生直接冲突,况其办法又无异夺中国人民之血汗以饱四国银行之贪囊,这自然会激起百姓的反抗。于是四省纷纷成立保路会,以咨议局为反抗运动的中心,而高倡“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之说。等到入京请愿无效,各地集会被禁,湖北的中产阶级遂已逼得只有“上梁山”之一途了!我当时曾参加游行,饿着肚子摇旗呐喊,闹到半夜才散;所以那时候一般人奋不顾身的情绪,是我所深知难忘的。
迎接革命
自保路风潮发生以后,武汉迄未十分安宁。伯有相惊、谣诼纷起,中秋举事之说传遍街头巷尾;汉口俄租界、武昌曹家巷、胭脂巷诸处的革命机关先后破获,益令人心惶惶。至八月十九日(彼时还未采用阳历,故本文所说的月日概系阴历)黎明,乃有在总督衙门照壁下枪毙彭、杨、刘三烈士,及半闭城门,严查行人之事。夜间将大索革命党人的话更传遍三镇,闹得我们没有辫子的人个个自危,以致起更(时武昌还实行打更的制度)不久,便已路断人稀,商店大半关门,住户且多熄灯,一时大有乾坤将毁,末日即临之势。果然刚过几点,便有砰然之声起自东南,连珠密发,比除夕的爆竹更为热闹。夜将半,隆然之声大作,我们全家俱在楼上凭栏探望,很清楚地看到一颗一颗的炮弹,带着一条红光,从蛇山上向督府方面飞去。经满清政府保管了270年,在世界上号称最古的宝座便随着这一阵砰轰之声,化为飞烟了!我整夜未眼,等到天色微曙,炮声已停之时,便出门探视。走到长街,见有些商店的门半掩半开,乃向几家有来往的店家探询,都说有臂缠白布的军人来过,说是革命,杀旗人,叫他们照常做生产,不要惊慌迁徙,致乱秩序。问到他们对这次事变的态度,则不约而同地说:“那些做官的,尤其是旗人,让他们干掉也好;只要不扰百姓,我们照做自己的事,管他们以后怎么革法!”这是当时武昌商民迎接革命的真实态度,可以说是历史见不到的实录。这充分显示出一般老百姓之毫无政治意识,自然更谈不上有何政治主张。他们却很厌恶满清政府,颇以毁之为快;但是对于革命运动却又毫无认识,根本就无法产生拥护或反对的观念;只要自己能照旧生活,便无妨对任何政权都暂时予以接受,而静俟其末将之演变。满清政府之一推便倒,民主政治之风雨飘摇,都是这样的民众态度所造成的。
起义后两三天,武昌可说成了全无政府的状况,一切衙署都是人去屋空,而所有的大街小巷,乃至藩抚衙门,都挤满了东张西望、面现惊奇、看热闹、探消息的老少男女。我已整天乱跑,寻觅我那时候认为有趣的资料,曾经看到几个被打死的旗妇,陈尸街上,两天未收,而臂上的金镯并未羽化;更看到藩库银锭堆积满屋。人人挤进去瞧,而不伸手一抹!(《清史稿》中有“变兵掠取库银”之语,不知何据,似未可信;因为既抢就会抢完,岂有第二天库中仍有很多存银之理?)这些廉节耿介的民兵真构成了一幅理想世界的蓝图,可惜极美丽的乌托邦仅是昙花一现;等到都督府一成立,权利之争即便开始,浸假而以暴易暴,竟亦莫知其非了!那几天的经过告诉我:人到非常时期,置性命于度外,辄能发挥出特殊的力量和智慧,表现出卓越的勇气与道德。若能培养这种如神的志气和无我的人格,使其进入“三月不违仁”的境界,再扩而充之,便可望达到安之若素、老而弥笃的地步;信如此,便人皆尧舜,修罗世界化为净土了。然而一时的清明总敌不过多种的诱惑,古往今来,有许多豪杰之士晚节不终,误己祸国,又何尝是其初衷本愿?克己太难,革心不易,追述旧事,感慨系之!
世相百态
在此时期,有两个人的行为曾给我以极深的印象。一是前方言学堂“教习”夏维崧先生:他是前清在圣彼得堡大学唯一得过学位的中国人,与当时汉口领事团团长俄国总领事的私交颇厚,遂往说服俄领,使其召集领事团会议,承认革命为合法的政治运动,而令各国炮舰严守中立,且让革命军武装通过租界,开往刘家庙一带布防。假使领事团当时对革命军略加阻挠,则“汉之为汉诚未可知”矣!有关民国革命的著述,用中英文字写的,多到可以覆盖天下之酱瓶而有余,却竟无一篇提及此事;要不是杨树人先生1960年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一篇讲夏先生的文章,这段很重要的历史事实恐怕就会永远不为人所知了。第二个是安陆府知府桂荫:他在各省均已独立,临时中央政府正在组织之中的时候,知清朝必亡,乃遣其子女离鄂,将印信交给知县保管,而与其妻寄住到府学教谕家中;数日后,两夫妇方于夜间同入文庙,自缢。《清史稿》倒为他立了一篇百余字的小传,但都写得不实不尽。传中称:“郧阳兵变,骤围府署”,其实安陆根本无兵,郧阳的兵更没有跑到安陆去“变”的道理,把一个自动殉节的人写成被迫缢死,岂不是冤枉死者吗?不错,拿现代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说桂荫是个顽固分子;但他顽而能“固”,竟“固”到本可不死,而偏要以一死来实践那食禄死事的信条,这样愚不可及的精神难道不比那般恬不知耻遗老们高出万万倍吗?况且“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这两种死法在道德上有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八月二十日上午,有个瘦小的老头子叫马臬台,朝衣朝冠的,抱着大印,坐在大堂上等人去杀。他原以为做大官的必死,与其让革命党搜索出来去处死,倒不如打扮成一副殉节的模样,岂不死得体面些,而且还可以留个美名?那知坐了半天,惹得许多看热闹的市民聚集署内,把他当作戏台的小丑看,而竟无人骂他,更没有兵杀他!后来他家里人打听到消息,说革命党人并不杀汉人,他才赶快入内易衣,溜之大吉。试想他那天果真被杀,不是就真成了一个“大大的忠臣”吗?《清史稿·忠义传》中的人物多半属于马臬台一个类型,是不应该拿来与桂荫相提并论的。
离城返乡
张彪弃军离鄂,武汉遂暂告无事,但报纸全停,竟致一切消息断绝;街上偶尔贴有一两条简单新闻,多空洞夸大其词,反足增人疑虑。彼时道听途说,都弄得惴惴不安。革命是否有人响应,武汉是否可免兵祸,这是人人关心的事,却得不到一总可以供给我们推测的资料;大家的情绪烦闷可想而知。第二件令人不安的便是全体公教人员同中小学生都成了失业、失学的游民,而这些人又多来自外州县同外省,若在武汉长住而无事可做,势必有无以为生之一日。我们在武昌也是侨居,自然很为焦虑。屡和亲戚同乡们商议,终于决定结伴回乡。彼时武汉间的电话常打不通,住在武昌,很难知道长江航运情况;于是全家乃先迁汉口,暂住旅社,以便接洽轮船。家里九大箱书及全部木器,则寄存到一个与我们有关系的学校里(后来那个学校被一军事机关借用,我们寄存之物便全无踪迹了)。三天后,我们全家六人同将近二十位的亲友便坐上一艘外国商船,离汉返宜。彼时宜昌已经“反正”(这是当时流行的名词)。秩序非常安定;人们的辫子已经剪的差不多了。同行的人,家都不在城内,遂分住旅社,各奔家园;和我家有点瓜葛关系的两对新婚夫妇竟从此永未再见,人生离合无常,真是思之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