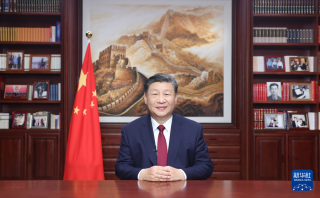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
辛亥革命网 2018-05-21 10:37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陈铭枢 查看:
一九○六年八月,我进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时,才满十六岁。此时清政府正实行所谓“新政”,两广总督岑春煊又是当时在南方实行“新政”最有力的当权派。陆小招考第一期学生时,尚不为一般人所注意;到第二期,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考场设在原来乡试的地方,足见清政府对此亦极重视。
我入校时,第一期同学尚未毕业,其中同盟会员仅有陈汉柱,何卓俦等人(何于二次革命时,被黎元洪杀害于汉口)。陈汉柱同我都讲“客话”,他经常向我宣传排满兴汉的思想,不久即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因为我是广东客家族,而广州同盟会秘密机关的主持人,也多是东江客族(如邹鲁、姚雨平、张酉录村等人),所以不久我就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组织联系。此后,我遇有机会,就向我所物色的对象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当时的宣传品主要为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和谭嗣同的《仁学》等,还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杀记》等小册子。我常利用星期天,约新入盟的同志到山岗僻静处填写盟书(,即誓词)。当时入盟的人甚多,且有一些富绅子弟,如李朗如为广州好几百年老店——“陈李济”如意油店的小老板,刘汉忠也是大商家的子弟。
在秘密机关里,姚雨平告诉我,我校将到任的新监督赵声,也是同盟会员,并说已向他介绍过我了。
赵声字百先,江苏镇江人,是由南京新军三十二标标统任内调来广东的。赵到校第三天,我就单独前往晋见,他毫不掩饰地用同盟会的“握手暗号”同我相见。我童年时随父读书(父为前清廪生)旧的东西给我不少影响。记得我同赵对晤时,曾涉及宋明理学家的言论,他听了立即正颜厉色地说:“中国的礼教,经过朱熹更是变本加厉,已成了吃人的东西。我们投身革命的人,对之应该深恶痛绝,万不能再受其毒害。”这好象是当头一棒,使我历久难忘。
赵生得身材魁伟,不类南人,长面竖眉,声音宏亮,眉宇间有一股威严之象,故大家称他为“活关公”。其时校内有一个学长(即排长)林震,亦同盟会员,因他的相貌生得与赵相仿佛,由于大家推重赵的原故,故对林也推重起来。赵不仅使全校师生倾倒,也受到新军的普遍崇拜。当时广州军人在各种集会时,都异口同声地夸谈赵声,开口“赵百先”,闭口“赵百先”,甚至有说成“我们的赵百先。”这种现象普遍流行于新军界,而以在燕塘新军的军官罗炽扬为最。彼时相交传述赵的轶事甚多。如说赵在南京任标统时,某日独游明孝陵,途中邂逅一人,见赵气概不凡,即趋前攀谈,问;“先生贵姓?”赵即以手指天答:“天”。其人再问。“大名?”赵复以手指地答。“子”,言毕即掉头不顾而去。这本是一种传说,但是大家因为推重赵的原故,津津乐道。赵在校中,对第一期学生甚感失望,他在公开训话时说:“第一期学生暮气沉沉,还不如第二期学生之有朝气。”他这番话对我们同期同学有极大鼓舞。学校的总办(即校长)韦汝聪,在性格、作风和思想各方面,都与赵形成鲜明的对照,韦重外表,讲排场,性格猬琐而庸碌,而赵则重实际,性情豪放,敢作敢为;至于政治思想,更如冰炭之不相容。因此同学们都爱戴赵而厌恶韦。某次校务会议,赵对韦竟戟指斥骂,使韦下不了台,结果闹到新军督办公署,赵由此辞职,后调任燕塘新军第二标标统。
赵离开陆小后,我与他仍有联系。我在白云山能仁寺养眼病时,介绍一个因闹学潮被开除的同学王鸾(同盟会员)同他见面,并请给王找出路。某日赵独游能仁寺(寺与燕塘军营毗邻,越一山岗就到了)适遇着我,乃共同漫步。时寺中有一和尚,俗名陆龙杰,为陆小第一期末毕业同学,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愤而弃学出家。其时他正在廊下临摹颜鲁公法帖。赵见其书法尚佳,就坐下同他攀谈,得知其身世,立即成诗一首;写成条幅送他,诗为:
愿力未宏因学佛,英雄失路半为僧。 月明沧海归来日,万里蛮山一点灯。
接着,赵又榜书“宏毅”二字的横披送我。以后我每一杯念百先先生时,辄把这首涛和他在廉州海角亭(我的家乡)所赋“八百健儿齐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之句,还有他送皖北友人(即吴樾)北上那首诗,一起联系来诵读,那首诗是:
淮南自古多英杰, 山水如今尚有灵。 相见襟期一潇洒, 朔风吹雨太行青。
在赵离陆小的前夕,我曾往晋谒,询及广州尚有何人可以联系,请予介绍。赵说:“现在广州的有朱太符(朱执信),其为人不以才气见长,但有学有守,可以信托,你可同他联系。”其时朱在广州某校任教员,家住城内豪贤街,他领导的秘密机关,就在附近。此后我常到他家或机关汇报工作。某次在他的机关里,见他与其他同志正在商量利用某青年女同志(她也在座)化妆成卖身的女嫁娘,以饵某富翁(时富翁在另一室,我也看见),俟身价入手,即设法潜逃。足见当时同盟会筹备经费之难。在离朱家不远的天官里,有一幢楼房,是由朱租来供新军同志活动的机关。我因得朱的介绍,曾去过多次。此时,我曾因朱的介绍,结识了当时新军界中的另一杰出人物——倪映典。
倪映典为皖北合肥人,曾在安徽新军与熊成基等进行革命活动,已升任至管带(营长),后因有人告密,乃改易姓名,出走广东,仍投入新军。他在广东新军,初为见习官,后任排长,在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也是天官里机关的核心人物。倪生得同赵声一样,身体修长,具有一种刚强气概,虽不如赵声的魁梧,而英姿飒爽,一望而令人畏服,处世接物也处处表现出一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就我少年时所接触的人的印象而言,他使我终身难忘。我曾向倪介绍广西博白县的朱锡昂入盟,朱锡昂为广东高等实业学堂的学员,同我很相投,经我动员后,愿意入盟。当我带他到天官里去见倪时,说明他是来入盟的。不料在填写入盟书时,朱仅填他的别号“拭生”来代替本名,倪顿感不满。俟朱离去后,倪用极严肃的口吻责备我说:“你不应该把这种人带到此地来,象他这样顾虑多、缺乏勇气的人,怎么能搞革命呢?”他又说:“象这样的情形,你应当先同他讲清楚,怎好这样盂浪呢?”我受了他的教训,感到难受,但从此对他更加敬佩。朱锡昂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家乡博白县被国民党反动军队俞作柏部逮捕,旋即慷慨成仁。历史作了见证,朱并不是倪所说的那样人,但在当时残酷斗争的情况下,倪对我的责备是正确的,因我没有把入盟手续对朱讲清楚。
一九○九年的旧历除夕,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时倪已离开燕塘新军(因被告密而革职),经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问,负责策划新军起义。当军警突然发生冲突,倪恐秘密泄漏,曾到香港总机关商量对策。当他匆匆返广州时,事件已经扩大,秘密已无法保持。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倪只身驰入燕塘军营,适有管带漆汝汉,正集合士兵训话,意在弹压。倪突至,真象飞将军从天而降,全体士兵皆跃然而起。倪先发制人,立抽出手枪,当场将漆击毙。倪振臂一呼,群起拥戴,步、炮、工、辎各营约二千人,随倪整队出营,迅速占领了东门外钱局后的小山,准备攻城。时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率队前来镇压,并派出倪的同乡管带童长标出来伪作和解。倪大怒,策马立阵前,晓以大义,慨慷激昂,敌军闻之亦为之动容。敌乃乘时发炮,倪被击坠马下,为清军俘去,最后大骂不屈而死。
此后不久,我在陆军小学毕业了,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时赵声已离新军,住在香港的时候居多。我在南京,从与赵及广州有关方面通信中,对南方情况仍时有所闻。一九一一年春,我知道从海外,特别是从日本、南洋一带回香港来的人甚多,这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候。我断定广东将有新的举动,故向学校请了十几天的假,托辞回南省亲。行前我又写了一函至赵声,说我就要回来了。我到香港后,刚下船即驰往赵处,见赵着日本和服,高踞桌上,同围着他的人高谈阔论;这些人也着和服,一望而知是刚从日本回来的。经赵介绍后,知为福建的方声洞、林时壤、李文甫等人,是回来参加起义的。赵随即对我说:“你的信我已收到了。”我说:“我回来是要求参加起义的。”赵带着严肃的口吻说:“你们军官学生,是将来革命的种籽,以后推翻满清,掌握军队,全靠你们这一批人,怎好轻易牺牲呢?况且这次起义,成功与否还不可定。你赶快回去吧!\我见他态度严肃,语气坚定,故未便坚持,旋说:“我请假的期限还未到,我想进广州去看看情况。\赵同意后,当天我进了广州,在秘密机关会着姚雨平等人,他们也催我赶快回学校。我住了一夜后,次日到港,又逗留了两三天。当我乘船抵达上海时,刚登岸,打开当天报纸一看,知道广州发动的起义,于昨日(三月二十九日)遭到失败,牺牲的同志甚多。这个噩耗,有如晴天霹雳,使我万分惨痛。
是役失败后,赵由顺德经澳门转回香港,旋即大病,不久即逝世。闻其将死时,曾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我自闻百先先生之死讯后,每与同志们诵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老成凋谢,后生罔识,向慕之忱,日远日亡”之句,辄相对怆楚。这不仅是因他的革命言行感人之深,实因他早丧,乃革命之一大损失。
不久,谭人风来南京看我,谈及起义失败经过。谭非常激动地破口大骂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说他负责指挥的那一路,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谭对其他好几路的负责人,亦有责难,对姚雨平本人,也很不满。
自此次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仍在海外积极活动,黄克强先生将同盟会机关迁到上海。总机关以黄为首脑,下分五部,其中负责组织的陈英士,负责交通的谭人凤,都到南京同我见过面。
其时,我在南京陆军中学,仍积极从事同盟会活动。开始时,对外联系全由我负责,以后会员增多,如四川的吕超,福建的金仲贤、吴兴五,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的人亦有,又增加任铖(任援道)与我共同负责对外联络。
同年八月十五夜(旧历)谭人凤突然到南京,约我到他住的旅馆相见。他谈到立即要去武汉,因为武昌同志将发动新军起义,总部认为各方面的部署还未就绪,此时不宜轻动,故他奉派前往劝阻。谭十六日乘船西上,计算行程,尚未抵达汉口,而武昌新军首义的旗帜,已飘扬在黄鹤楼的上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