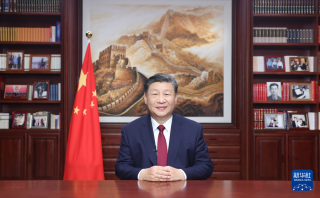云南起义史实之淆乱与订正
辛亥革命网 2018-06-20 09:17 来源:云南文献第40期 作者:白之瀚遗作 查看:
历史家之纪载一件大事,类皆以此事件中心之总揽(即领导)人物为目标,此非尽由英雄主义或个人本位之见地;实缘事态繁杂,必用一二主脑以为代表,乃可简化而包举也。远如驱逐胡元之揭明太祖,解放黑奴之首崇林肯,近如战胜洪、杨之标举曾、胡,马厂起义之归功段氏,古今中外,殆莫不然。护国一役,唐公既为发难唯一之地位,复掌总揽全局之事权(蔡、李各任军长,负一方面军事之任,是为分司;唐公身任都督,负统筹全局之责,是为总揽。)且歃血立盟者唐,领衔付贼者唐,而西南合组政府之首脑又复为唐(抚军长)。无论法理事实,均应以为此役之代表。此就属于人者言之也。云南地瘠人稀,向为受协省份(清代由鄂协济)。民初本省岁收,经常不过七八百万,人口仅及千万。以如此贫而且寡之人力、物力,与富厚雄强之袁逆抗,其将举鼎绝膑,实为必然结果。当时罗掘之苦,拮据之情,至将全省教育款项完全提用,学校一律停办,公务员只领少数伙食,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亦准避免,可想见矣。若夫征募壮丁,川流不息,入川一军死亡兵额,前后不下一万,他路可知。其中多有曾受教育之学生,尤可痛借。至供给转运,及龙氏入寇,因此役而死之人民尤难以计算。山国货运,纯恃骡马,起义悉被征用;自经此役而运道阻滞,商务萧条,数年不能恢复。本省公私经济,受此影响日陷绝境,纸币低落,财政枯竭,迄于十七八年犹未整理入轨。当时之民,毁家以助军糈,殉国而遗鳏寡。大功既成,穷苦无告,所谓「对国为扶危平乱之功臣,对滇为荡产破家之败子」者,其言不无偏激,其情实亦可伤。此就属于地方者言之也。惟其难发自滇,故国会之规定国庆,不曰护国而曰「云南起义」;惟其事由于唐,故尔国府之崇德报功,不及其他而独表扬唐氏。定论千秋,宜无所谓淆误矣。乃因当时政客故弄玄虚,伪造蔡系主动唐为被动之说,少数书商不暇详察,竟于中小学教科书中,将此役完全属诸蔡公一人,而将唐公、李公一概抹煞。甚至标题直曰「蔡锷举义」,并云南人民亦似不足指数。坐令通行之后,辗转沿袭,谬种流传,至今犹未纠正。兹就经过事实,予以客观辨正,所以尊国典,求信史也。今先述其淆误原因如下:
一、淆乱之起,以梁启超始作俑,而其影响,则以所着之《国体战争躬历谈》为最巨。按此役梁于事前曾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之刊布,梁、蔡师弟先后脱离北京,筹划南行,与滇主张正相默契。而滇中同志,根本即认此事为举国人民应同争回国家人格之公共大业,凡属反帝,莫不欢迎;况以梁、蔡关系,尤常合作,故唐之对梁,尊礼备至,且曾派员迓请来滇共策大计(后因入桂,未能践约)。梁对唐及滇人,亦屡致电函,极表推崇感动之意(来函中有「以一隅而抗天下,开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不计利害为天下先,拯国命于垂亡,当为全民感谢」之语,唐曾影印遍发军民。梁氏书札均存东陆图书馆,亟当检选刊布)。诚可谓道合志同相处无间矣;所以始合终离,且至反唇诬诋,此中实有故焉。始缘蔡困大洲驿时,屡电乞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旋见有新编组及出发之军,益疑唐尚有余力,厚此薄彼,曾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相责让。加以罗、戴、刘、周(骏)之间,挑拨大有人在。以唐地位关系,无论何事何言,莫不以为尾闾。职是,蔡屡密电肇庆,抒其愤懑(按当纳、泸酣战之日,正龙、杨入寇之时,叶、黄、赵、庾诸军,皆自蔡出川后,陆续凑集而成,人械均甚劣弱;而分遣出援之师,亦系陆续筹编就道。以财械交通之种种困难,断难从成事之先后迟速加以猜侧。总之,统筹兼顾者之易致逆尤,乃属当然之事。而蔡公身当矢石,焦劳过度,偶有不谅,吾人终当曲体之也。)梁遂深怀不满,及军务院议起,梁派黄群到滇,以桂陆之独立出兵及提挈两广,均系全局安危,唐之学养,远胜于陆,请以抚军长让陆。滇中军民闻而大哗,以此职非有虚荣大利,诚恐名实一紊,将致后人误会,使滇沦为附属,遂引梁氏电函推重原语,纷电诘问。梁既以此许陆,又不得不从公论推唐,两面为难,备陷窘境(其后桂、滇不睦,至于在粤交兵,祸根实始于此,谋国者可不慎哉);且狃于过去之言听计从,今忽受此重大打击,益觉意外难堪。遂由不满而成宿怨,是为发生嫌隙之真因。自此往还顿疏,仅未破裂耳。迨护法师兴,梁嘱陈廷策向唐劝阻,唐坚执不从,且亲督师至渝,于是梁益愤恚,而彼此之声问遂绝。其后二年,梁氏到宁讲学,乃有《躬历谈》之作,则不啻为上述种种嫌怨之总表见焉(关于蔡在大洲驿及梁阻护法二事,当时报章杂志,既可寻绎,且有梁氏《全集》暨《盾鼻集》、《躬历谈》并松坡《军中遗墨》等,可资考证。惟军务院一段内幕,当时因恐袁、段窥见破绽,未尝发表,几成密史。然当时各界既有质问梁氏之电,则昆明、肇庆两地电局,当有原底存档,况参加此役之各方同志,尚多健在,知者谅亦不少也)。自此书出,而是役真相完全颠倒,盖梁氏蔡氏既有进步党人为之到处宣传,复多往来于交通便利、报纸发达之地,滇则僻处边隅,民性惟重实际,在外如京、沪各地,从无宣传组织,偏远隔离,几同世外。《躬历谈》发表之后,虽曾有人著文反驳,但只登诸本省报章,且梁素有文名,又尝亲与其事,故能为所掩蔽而贻误至今也。
二、政治内幕表里悬殊。以欧美人民经验知识之富,尚多隔靴搔痒,何论「莫谈时事」之吾国?况袁逆作风,尤喜变乱事实,以便私图,当时报纸复为收买,令人益难捉摸。一般人民既无正确消息,惟有就其表面迹象以为判断。当蔡氏京寓被搜查时,人皆传其由于反帝,及夫离京南下,以曾督滇之故,又皆测其赴滇。从此心目中已先存一「蔡氏到滇反袁」之成见。有电既到,蔡果列衔,人民以为已与传说无异,既愈加重成见。而袁以镇定人心及离间作用,复一再布告捏称:「蔡锷到滇游说唐继尧独立,其实唐非出本心,全由蔡锷胁制主使」云云,又以为与其判断符合,更自深信不疑。加以漾、有两电,感日檄文,进步党人既早宣传为梁所撰,梁复收入《盾鼻集》中。缺乏阅历之人,遂谓此等小事且然,不暇深思说考。及后梁氏著作,大吹大擂,从不见有何人加以辩正,遂致愈久愈晦,习为固然。夫具明晰头脑以知人论世者,曾有几人?据表面先入之迹象,堕仇口狡狯之术中,在彼时情况下,吾人亦惟有寄以「君子可欺以其方」之心情而已。
三、在行「国宪」前,所有中小学教科书,皆由书商自编,呈部审定。无论稿费有限,难觅专家,即有少数备具作史之长之人,而民国史事之修撰,既无专司,散乱分歧之材料,又未整理,学理虽优,研讨不易,欲其征信,岂非梦呓?其无编译机构之书肆,则彼袭此抄,更难语此。又况出版界中,多与梁有联系,非仅不为矫正,且恒假以自重。有此数因,则教科书之歪曲淆乱,殆为势所必然。今以客观事实,针对淆乱各点,逐一辨正如下:
(一)此役集合全国反帝同志,奉义而趋。其共同旨趣,惟在各尽其力以争回原来之共和国体,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岂特唐、蔡之间,无所谓主动被动,即勤职殉身之员与认捐输饷之民众,亦无所谓主动被动。有如此次抗日,纯为正义所驱,若真出于勉强,不惟意志决难如此坚强,即收效亦决难如此圆,此我国民不淫、不屈、不移之真精神也。乃竟扬已抑人,妄为品第,非仅厚诬唐氏,且是损我护国军民全体之尊严矣。
(二)此役不分轸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渊源,考其质量,要以国民党为中心主干。前列军府军队组编表,其主要人物之国民党籍,既占十分之八。而在各地艰难起事者,又尽属国民党人,事实所示,可为铁证,何得掠美贪功,攘为已有?
(三)在事诸人,分工合作,各有价值,不容轩轾。然若就职能言,则唐氏总揽全局,实为适当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则唐、蔡、李同为此役首领,何得独尊一蔡,抹煞其余?
(四)滇省先遣之邓、杨两支队,自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九日出发,至十九日开毕(《护国军纪事》载有《中华新报》所登护国军一兵士由昆明出发日期及沿途作战攻克叙府之日记,此非本省事后之著作,而为当时日报之实录,有此一书可为佐证)。而开拔之前,尚需作种种预备(彼时交通艰阻,军队设备简陋,事实所限,实难朝令夕行)。计其时间,实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一旬以上。即以最后尾队而论,相距亦在一日以上。蔡且未见其行,遑论主使策动?(滇越火车,由阿迷抵昆明,均在下午七八时,冬季尤晚;而早站行路,例于天明动身,军队尤早)又蔡公于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出发,而先遣军是日已抵川边之新场,二十日且克叙府(所述日期,均有当时各报记载可查);此尤足以证明唐早有决策,先期遣派之不虚。按昆明叙府旱路,马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列休息一日,故最速须三十二三天始达。此路地旷人稀,军队以给养转运之繁多,且系沿途转战而前,需时又当倍之。准此,则一月二十日之克叙府,其由昆明出发,至少在四年十二月初间;里程具在,尤可从事实得到证明。若为被动,焉能占此先着,迅赴戎机?
(五)缪嘉寿、吕天民、李宗黄、赵伸等之分赴各地,担任起义筹备工作,远在蔡公抵昆之前三个月,起义时多尚未归,故十二月二十二夜,上校以上之歃血宣誓,缪等与先遣军之刘、邓、杨三人,均未能列席(有各种记载及当时报章之名单可证)。若为被动,则事前不应有此种派遣。若未派遣,则此单不应无名(诸君职位或为上校或在上校以上)。事实俱在,可为反证。
(六)李协和、程颂云、熊锦帆、方韵松、吕天民、但恕刚、王伯群诸公,皆民党要人,或先蔡入滇,或同时到达。若谓蔡与滇省军队有关,以主动此役而入滇,则无主动之名且系初来之诸公,亦能入滇,又将何说?
(七)唐氏若非早日决策,渴求同心,则决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无诚意,则应付之术,头头是道。无论只图私利者,不难因而缚献,立博王封;即兼顾友道者,亦可恫以危词,拒使他位。欲骑墙,则设法稽延其行,以留余地;欲取巧,则坐视周、张狙击,诿为不知。惟唐刻意相近,视友如己,派遣其弟,保护惟恐不周;且以所部十分居七最称精锐之兵力,自动属诸蔡公,而甘留寡弱以自守滇。诚心实虑,惟忧此事之不成。苟为被动,安能如此精白专纯乎?
(八)若再分析言之:谓蔡主动之说于到昆以前为之耶?则所凭借不外函电文字之耸动,区区纸片,竟收如此奇功?岂非笑谈!且自京寓被搜后,根本已难通讯。谓于到昆以后为之耶?则无论用何方法,施何手段,断难以灭族屠民之事,于匆匆两三日间(二十日到昆,二十三日即发漾电),使人一致服从。且果如是,则所致各方电函,必将略及运动说服之经过,今所有梁、蔡作品中,绝无丝毫游说策动之痕迹,而蔡电反有「多逾初望及先遣已达滇东」之词。其为荒唐,不值一辩。又或谓蔡有旧部关系因而胁迫耶?则蔡离滇已将三年,当时带兵之上中级军官,已经人事之再三更调、其势已失衔接。且起事前之师长为张、刘(祖武),而起义后即以所部改隶顾、赵、刘(云峰)等,胁迫之说,既须利用现任统兵之官,何以起义反致解去兵权(当时因顾、刘善战,故使统兵,而调张、刘幕职,于此愈见当时将士同心,唐可任意更置也)?又况古今来部下建议而上级受纳者,史不绝书,但能抉择可否,莫不以善归之。即此明目达聪之风,已是表驭群伦之度。斯为胁迫,只见其妄。更或谓由遗爱拥戴耶?果尔,必有各界开会请愿之举,何以绝无所闻?此其幼稚,更不待言。总之,无论作何说法,举凡时间之距离,部署之安敏,在在皆可以为反证。倘非主动,万难如此神速,是则不攻自破者也。
(九)起义之漾、有两电及感日覈文,并致各国通牒各公使照会等,均梁在外撰就(均见《盾鼻集》。但感日檄文,则唐公不甚满意,特请任志清先生另撰,仅有数句沿用原稿。因梁在外先已发表,故报章前后所载各异。此虽文字末事,亦足以见唐之不尽听人主张也),交蔡带滇发表。若非预知唐已决心,何肯虚耗精神,先作此举?
(十)护法议起,梁嘱陈廷策劝阻,唐坚不从,以梁对护法之不能阻唐兴师,愈足以证唐于护国之决非舍已从人。
(十一)梁于起义时,对唐颂扬惟恐不工,决裂后则诋毁弗遗余力。夫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求知则可,论人则非。以其前后之矛盾,愈见其言之支离。
(十二)唐、蔡同学、同官,交谊至厚。蔡之于唐,始则特命统兵以援黔,继则密荐回滇以自代。唐之于蔡,既屡次派员寻访,竭诚以迎其入滇,复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权之旁落,两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笃,实非势利之交所能妄测,尤非小人之心能忖度。蔡于抵昆时对同人之第一语曰:「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们已经样样都准备好了。」想见其欣慰之情、内心之喜。唐于蔡病殁后对滇民之演讲词曰:「松坡之死实是国家最大损失。昔时地区起义,我二人同心救国,外间小人,竟有松坡为主动我为被动之说,本省军民深抱不平。其实我与松坡久共忠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要说松坡是主动,我当然也是主动,要说我被动,松坡当然也是被动。一死一生,乃见交情。我滇人对松坡之死,应该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论,毁誉不屑计较一时。要知道云南起义,乃全体云南人民自立自做之事,这一点既然无人能够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还介介呢?」足见其器量之大,见地之超(滇中情事,外间虽多隔膜,但亦不乏批判明允之人,如延庆马大中所着《大中华民国史》,其论蔡、唐曰:「唐承蔡后,整武经文,论唐之才或在蔡之下,而其器确在蔡之上也。」国中曾与两公共事及留心大局者,亦多持同样论调)。唐、蔡情义若此,中间偶有误会,既同由于为公,终当涣然冰释。观乎唐及滇人,对蔡始终爱重,未尝因为有被动谰言,少受影响。则蔡公九泉有知,闻此主动被动之说,亦必为之踌躇不安矣?盖知人论世,要须综览平生,体会情境,方能把握大处,不流穿凿。彼纷纷者之信口雌黄,亦徒见其枉用心机,毫无是处矣!
总之,真确实在之事,譬如四肢百骸之运行,但能正常不变,自然脉络贯通,处处顺理成章。虚伪捏诬之言,则如借用他人之衣履,任其精于弥缝,终必露肘削足,罅漏毕是。试观上述论证,此理益觉显然。夫护国大功也,主动美名也,如康(有为)之言曰:「我命梁启超为之」。梁之言曰:「我命蔡锷为之」。罗兰夫人云:「自由、自由,多少世人假汝之名以行。」湘绮先生云:「功名二字,害人最毒,即贤者当之,亦违却本心。」康、梁且然,又何怪于绛灌辈之拔剑砍柱乎!
编者注:
白之瀚先生,护国首义时任唐继尧的机要秘书,负责起草和翻译电稿。护国首义后任云南督军署秘书长。本文节选自白之瀚先生的《云南护国简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