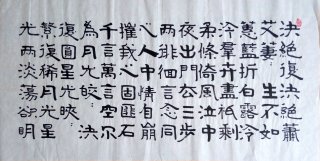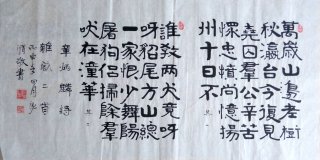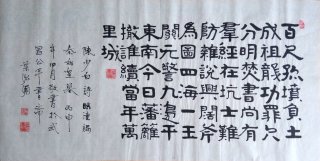我的父亲王维沈(2)
辛亥革命网 2017-08-22 10:26 来源:《嘉兴市志资料》第二期 作者:《嘉兴市志资料》第二期 查看:
我父亲自从1900年在杭州为了研究时事,富传革命思想,自发集合10余人组织“浙会”以来,一直至1903年初夏,成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为止,他从一个爱国有志的知识青年开始,逐步步入了爱国反清的实际革命行动的机关了。军国民教育会规定要派遣会员回国策动起义(称为“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当时派往湖南的会员为黄轸(改名兴,及改字克强)、陈天华、刘揆一;派往江浙一带的会员为龚宝铨;派往安徽的会员为程韵苏;派往南洋一带活动的会员为董鸿祎、王家驹;还有一些会员如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也先后派回国以讲学为名,进行鼓吹革命宣传。自此以后,我父亲即往来南洋、日本、以及国内诸地更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秋季,我父亲从南洋回到东京,曾与在东京的“浙会”(即“浙学会”)的成员,先后两次在我父亲的寓所召集会议,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有蒋尊簋、沈瓞民、许寿裳、王嘉袜等10多人,会议讨论决定,必须另外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一方面加强革命宣传,一方面发动装武起义。并计划在浙江等省实行武装割据,作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根据地。而目前仅这10多个人,力量太单薄;必须再扩大邀请一些浙江的革命志土一起参加。于是在会后,大家即分别联络当时在东京的浙江人,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当“浙会”在东京我父亲的寓所召开第二次会议时,陶成章等人就已参加了。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计划,在这次会议讨论后,乃决定派陶成章、魏兰去浙江、安徽;派龚宝铨去上海;派沈瓞民去湖南,分别进行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的工作。其余人员,暂在东京加强革命宣传,为武装起义作好各种准备,或参加别地的武装起义,共谋推翻清廷。
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季,我父亲突然回到幼时居住的盛泽镇家中,并且手臂围了纱布,由于这一段时间,我父亲没有信息给家中,家中仅在这一段时间前,接到过寄来几本日文书本,还以为他失踪了,现在看到他回来了,又看到他的手臂 围了纱布,经询问情况,他只回答说:“曾去过南洋,以后仍要去日本的,手臂之伤是回国时跌伤的。”家中人也就不迫问了。但后来在家养伤休息期间,他对他的妹妹(即我称八姑母的),始吐露了真情,原来他是去参加了湖南长沙起义受伤的,由于这次起义,他中了枪弹,并跌伤了手臂,是逃回家乡的。现在我阅有关辛亥革命史书的记载:“长沙起义,是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奉日本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之派,去往湖南为‘运动员’(‘实行员’),准备在湘起义,当黄兴等到达湖南长沙之后,立即做了许多积极的准备工作,并再发电东京,又先后邀请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一些会员,也去长沙一起参加起义。这次起义原定的计划是准备在是年11月l6日(即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十月十日)当西太后万寿节之日,在长沙起义。在此之前,先在省城万寿宫之里殿下,预藏大炸弹一具候万寿节日,湖南全省文武官员届时必在皇殿行礼之时,即行燃放炸弹,以期一举炸毙清廷官吏,同时即宣布起义,并预先布置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处的起义人员,在是日分五路起兵,一起起义,并首先占领长沙;但是不料未到11月16日之期,即被清廷得知消息,因之,清廷长沙知府立即开始捕人,并把已捕去之入,反复酷刑逼供,再把逼供所得之准备起义人员,按名索捕,一时急于星火。当时,主帅黄兴于l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突然有差役前往逮捕,幸黄兴乘间避开,未被捕去。过后,黄兴即化装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后再逃往日本。当时清廷湘抚在长沙城内,即予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派兵查缉各党人寓所,全城骚扰,差投之捕人,真似风声鹤鸣,几乎草木皆兵,于是原准备在长沙起义之人员,各各被逼迫星散逃遁。”我父亲逃回家中后,对他的妹妹(八抹)吐露了是去参加长沙起义的真情,当在长沙被迫星散逃遁之时,我父亲被迫捕之兵土发枪中弹及跌伤手臂,最后总算脱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父亲避居在家养伤时,除妹妹(八妹)外,不敢将此真情对别人讲,盖担心如万一被清廷知悉追究起来,他是参加长沙起义的革命党人,必会受到斩首之刑,并月.或甚至株连九族的。后来,我父亲在家养伤了一些日子后,其手臂跌伤之处渐渐恢复,但上身所中之子弹,因不敢就医,一直未能取出。其时我父亲与他八妹均未结婚,八妹亦在其清贫的兄嫂下生活,自然难以挽留,我父亲在盛泽养伤了一些日子后,就义离别家中去上海,再去日本,继续干革命工作。
在1903年夏,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龚宝铨回国为江浙一带之“运动员”(“实行员”),但至是年秋,龚宝铨尚在东京,其时他又参加了“浙会”在东京之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浙会”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计划,曾经决定要在上海等地进行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的工作,并派龚宝栓去上海。后来,龚宝铨返国,在上海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至于参加“浙会”在东京之第二次会议,曾被派往浙江、安徽的陶成章、魏兰,回国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结交会党骨干,做了大量工作后,在1904年冬来到上海,当即与龚宝铨密商,如何按照东京“浙会”的原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为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作准备。正在此时,著名学者、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恰巧从青岛回上海,得知消息,即一起参加,于是经讨论决定,把已在上海建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之时,是在1904年(元绪三十年)冬季。在成立之后不久,陶成章和魏兰先后到达东京,这时我父亲已是去湖南参加了长沙起义负伤之后返达日本不久,大家这时相见后,即在东京与我父亲等一起进一步相互筹商,决定建立“光复会东京分部”,当即在1905年2月成立,并推举王嘉祎为光复会东京分部负责人,主持光复会在东京的会务。其时先后加入光复会东京分部的会员有周树人(鲁迅)、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等人,其中有的人即是早先与我父亲一起在“浙会”时的会员,也有的是该时新参加的。这样,东京与上海两地的光复会就开始一起为革命工作而努力。以后,这些人都为推翻清廷而进行了各种艰苦的斗争。
1905年8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这三个革命团体,及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所有这些革命团体在日本的成员,都加盟为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并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当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有l00余人,会员籍贯遍及全国17个省。一年后,会员人数发展极速,已超过l万人,我父亲与黄兴、吴敬恒、钮众建等,都签写盟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我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时,是用他的别名,即“家驹”也。
由于清廷驻日公使阻送中国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军事科之事,和留日学生抗议颁发“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之事,当时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很多愤极,相率回国。我父亲亦在1905年(光绪三个—年)冬,离别日本返国,后来又去南洋,一方面去宣传革命,一方面去南洋爪哇泅水埠华侨小华学校执教。1906年(光绪三十二)12月初,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三地联合举行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简称:“萍醴之役”或“萍乡之役”。这次起义,有同盟会会员杨卓林(字公仆、湖南醴陵人)等。原已约江浙一带光复会首领集议于上海,会商谋响应事,当时我父亲接悉后,即返国,与章太炎、敖嘉熊、秋瑾、陶成章、龚未生等人,在上海会集讨论如何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这次起义,原定于年底乘清吏封印过年的时机,但由于当时清廷该三县的当地官厅已在捕人加密,乃临时决定提前于1906年12月4日由萍乡矿工首先发难,湖阳、醴陵继之。起义一开始,不到10日,起义军人数即已达3万余人。原定的计划是分兵三路,即:一路据浏阳、醴陵攻长沙;一路取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路由万载、宜春东出南昌,进取江西。在这次起义的开始数日,即连克多地,声势极浩大,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摇撼了清廷的反动统治。这次起义,坚持了约近20多天,但后来被清廷以更多的兵力,约有5万人左右进行围剿,起义的人民先后被杀者达万人之多,至该月(12月)的下旬,起义乃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清廷一方面在派兵围剿萍浏醴,一方面更饬令各地官员加强防范镇压各地人民对起义的响应,以致各地的响应者,都相继失败,在革命党人中有多人都因而陷身牢狱,被监禁,甚至有被捕后惨遭杀害的。我父亲等人,当时在上海集议谋响应,亦以事败,乃只得即予迅速分散避匿。我父亲当时是避居在嘉兴乡间马厍汇,幸免于难。嗣后,我父亲与同盟会会员、光复会会员经常广泛联络,继续奔走革命,不遗余力。
民国成立之后,在民国元年1月,我父亲即应邀汪浙江省军政府秘书,时浙江省军政府都督为蒋尊簋,蒋都督亦是留日学生,并同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与光复会会员。曾听得我母亲说过:“我家那时是住在杭州,蒋尊簋都督常来我家玩的,他是浙江诸暨人,常穿军装,是武人,性甚直爽。”蒋尊簋任浙江省军政府都督及我父亲任浙江督府秘书,都仅约半年余,即辞去;我父亲即改任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多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时,我父亲是用他的号,即“伟人”也。嗣后,去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并曾参与调查日本中国由学生等事。其对,周树人(鲁迅)亦在教育部任事,为当时之同事也。
我父亲为了革命常四处奔走,置自己生命于不顾,他为革命献出了毕生精力。早年,他在参加湖商长沙起义时,身上曾被中枪弹,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未能取出,延至后来,不幸在某次身受感染时,”腹部受枪弹处创伤复发,最后腹中剧痛,翻复床篑,竞成生命无可救治。最惨者,在临近去世前,腹中剧痛甚烈,他面对我母亲高声长叹喊叫:“王维忱一世做人完了!”连续三声,大叫呕血而亡,极凄哀也。此高声大叫之惨情,我长大后,母亲曾当面对我讲述过数次,我一直记忆很深。我父亲在世之时,反对清廷专制腐败,而当处在北洋军阀压力之下,总冀谋今后再能联络革命志士,共同来铲除军阀,但是革命之志尚未能完成,而自己体内枪弹却创伤复发,悲生命之短暂,终未能完成革命之志也。据我母亲言:“当时在病床上,其身体之痛苦状态和哀叫之凄切声音,睹闻之下,真是极为悲惨之至。”我父亲终年仅四十有八岁。谅如无子弹伤发,可能生命尚不致如此短促,最后遗剩寡妇及幼小的子女而去世矣。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携着搀的、抱的幼小子女们回南,悲伤地把父亲的灵柩搬回家乡,葬入王江泾商花乡墓地:当时从北京开出的“灵枢专车”一路南下时,沿途都设祭吊仪式,直至家乡。此系当时的革命同志,感到我父亲一生为革命,而终以起义时受枪弹的创伤复发致亡,甚为可怜,乃沿途设以“路祭”以悼哀念也。